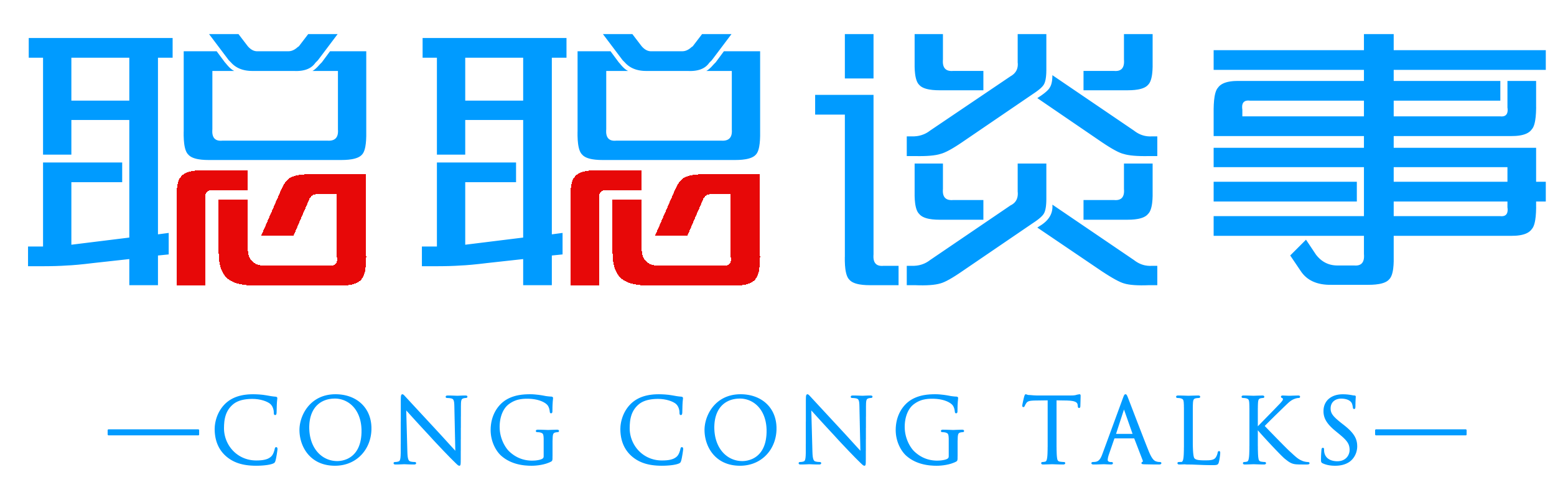被网贷“网罗”的大学生
今年2月的最后一天,在母亲的帮助下,程莉终于还清了网贷,此前,她曾欠下花呗、白条、分期乐等7个网贷平台累计四五万元的债务。陷入网贷的泥潭中,她身心俱疲,她发誓,除非买房,以后再不贷款。
诱惑
2017年刚上大学,程莉就已经从广告中接触到了花呗,几个月后,她在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开通了花呗。“正好那时候支付宝做活动,用花呗付钱的话有红包。”程莉说,不久她就习惯了这种付款方式。
程莉第一次大额网贷消费是一块手表,价格上千元,接近她的月生活费。
程莉就读的大学离家不远,她经常花一个半小时乘坐高铁回家,当时一千五百元的月生活费对于她来说是很宽裕的。程莉本打算用花呗一次性买下手表,等下个月生活费来了再还上,但在这时,家人对于她生活费的限制突然变得严格起来,如果用下个月的生活费还上花呗后就所剩无几。
她选择了分期。这笔分期持续了不到半年,每到月底,程莉总是生活拮据,连出行坐公交车都要室友帮忙付款。而在没开通花呗之前,她总是先充校园卡,每个月的衣食住行完全不成问题。
在这次分期结束后,程莉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超前消费模式满足了她的消费欲求,并且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驾驭这种超前消费的行为。
像程莉这样的大学生是不少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群体,在花呗、白条、分期乐等网贷平台均有学生身份认证,通过认证后,用户能享受到信用值提高带来的贷款额度提升或购物免息等权益,如分期乐通过学历认证后,最高可以直接提升3000元贷款额度,支付宝补充学历信息后,可以提升芝麻信用分,更高的芝麻信用分对于花呗贷款额度提升以及商品免息均有帮助。

泥潭
程莉开始背上“巨额”贷款是在一次抽脂手术后。2018年元旦,程莉和男友分手,失恋后她开始对自己的身材感到失望,抽脂的想法在她脑海中不停浮现,几个月后程莉终于下定决心做了手术。她记得这笔手术的费用不到14000,而她无法一次性支付这笔费用,于是选择分两年24期还完,每个月还820元。
后来她才意识到,本来不到14000的手术费,她分期后总共还了19680元,多还了五千多元的利息,实际年利率高达40%,而当初签这笔分期时,她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抽脂后的几个月里,因为腿围的减小,程莉需要随时更换不同尺寸的塑形裤,而每条塑形裤的价格不菲,都要几百元,她买了至少4条塑形裤,有1条仅穿了三四天就再没碰过。
然而抽脂并没有实现她想要的效果。做完手术后,程莉决定犒劳自己,“好吃好喝了两个月后,沉了十多斤。”程莉说。家人至今不知道程莉做抽脂手术这件事,她告诉家人手术在腿上留下的疤是蚊子咬的。现在回想起抽脂,程莉觉得并没必要,但她不后悔,“后悔也没啥用,就得自己摔一下才知道是坑”。
程莉在还抽脂贷款的同时还用着花呗,还款的过程整体还算顺利,只有一次她的抽脂贷款逾期了3天,接到了催收的电话,情急之下借了朋友的钱赶紧还上。
2020年3月还完了第22期抽脂贷款后,仅剩两期的抽脂贷款让程莉如释重负,这时她开通了分期乐。
分期乐的初始额度之高让程莉吃惊,新用户完善各种资料后能直接借到大几千元,而且分期乐的额度可以直接提取到用户的银行卡,用于其他消费平台和渠道。程莉最初抱着“只用几千”的想法借了2000元的分期乐贷款,她给自己定下“最多5000”的限制,而借到了5000元以后她又将这个限制改到了6000元,后来这个上限不断被打破。

程莉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为馋外卖,她又开了美团的网贷,购物欲望的日益增长,又让她陆续开了京东的白条和金条,为了补分期乐的贷款她还开通了有钱花,最多的时候,她同时用着6个平台的网贷,用它们相互填坑。
这时程莉的消费欲望如同一个填不满的黑洞,无论用不用得到的东西,只要她想要就会买,手持挂烫机、紫外线灯、烘鞋机……单单同一品牌的耳机她就买了4款,总价超过了3000元,她的室友曾问她“到底有几个耳朵?”
程莉不太会化妆,只常涂口红,她有10多只口红,而且多为限定款。另外,尽管不会用,但粉底、睫毛膏、眼线这些化妆品她都有。程莉还有一个爱好是闻香水,她有40只左右的香水小样和3瓶香水正装。
程莉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像疯了一样,走着走着就到市中心了,瞎溜达,想起什么买什么,好像是有人给我发指令,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去买。”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程莉未曾详细了解过任何一家网贷平台的借贷规则,也没有认真算过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更没有考虑自己最终该如何结清债务。
分期、提额、低价等这些字眼,将一些自制力差的大学生一步步卷入网贷和消费主义的漩涡。
在支付宝和京东等购物支付平台中还有着如“支付宝校园派”、“京东校园”这样所谓的学生专享平台,提供校卡充值、校园招聘、成绩查询等便利服务,还让学生能以学生价买到比正价便宜一些的商品。

让段胜陷入网贷泥潭的,是一部手机。2019年4月份,他用京东白条混合支付买了一部5000元左右的手机,1000元现金是他校外兼职赚到的,而另外的4000元则是通过京东白条借来的。
这笔分6期还的4000元贷款跟着他走出了校园。2019年6月份,段胜离校工作,一边是未还完的贷款,另一边是象牙塔外成本更高的衣食住行,更糟糕的是,他工作的单位在第二个月就开始拖欠他的工资,这让他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而在这时,段胜的公司出现了上门推销信用卡的工作人员。“身边的同事都有,我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儿,想着可以用信用卡一次性把白条还了,然后再分期归还信用卡。”段胜说。办下了这张信用卡,他还清了白条的贷款。
不经意间,网贷的雪球越滚越大。“我常常会有这种心态,比如说,我同时欠了网贷A和网贷B。由于还款日和还款金额不同,我就会觉得两头还太麻烦,这个时候经常有其他网贷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让我成为用户,我就会接触额度较大可以同时覆盖网贷A和网贷B的网贷C,一次性偿还A和B然后分期偿还网贷C,不过C的利率可能会更高。”段胜说,“但是缺钱的时候就不太会考虑利率,觉得一分期,利息也没有多高。”至此,段胜也开始了以贷养贷的生活。
惊醒
一年之后,以贷养贷的恶果终于浮现,程莉发现分期乐的坑填不上了,网贷不再带给她纵情消费的快乐,而是让她陷入还不上钱的忧虑中。她从有钱花借了2000元还上了分期乐当月的分期费用,但她明白这仅能解决一时的危机。
负债的这段时间里,购物欲望、定期还债、身材管理、学业压力、规划未来等难题,让程莉的身心都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程莉在这3年里的饮食习惯极不规律,有几天她整天只吃一块糖,有时一个人吃4个人的饭量,这让她的体重如同坐过山车。她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最后,她向母亲坦白。让她意外的是,母亲并没有追问她钱花到了哪里,只是问她欠了多少钱。“你的生活费不够吗?以后要是不够你给我说。”程莉的母亲说,“要学着理财,咱得清楚钱花哪了。”
2019年底,段胜治疗了4颗龋齿,这时的债务达到了让他焦虑的地步。2020年,段胜的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债务没有逾期但也没有偿还干净。
1月,段胜在总结债务明细时发现,以前他不以为然的利息竟如此之高,他所有平台的利息加起来一天要还45元,这甚至高于他每日的生活支出。
因为要还款,段胜整个人都处于无力失望的状态,他努力保全这份他并不满意的工作,没有勇气跳槽,因为换工作和搬家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失去了自信,越来越胆怯。”段胜说,“再这样下去,就是在用自己的青春给网贷打工。”
逃离
2月26号下午,程莉与母亲算清了她身上背负的所有债务,总共33514元。程莉用母亲转来的钱立即结清并关闭了花呗、美团、白条、有钱花、分期乐等,一次性结清的方式还让系统为她“贴心”地减免了总共五千元左右的利息。至此,程莉负债的日子结束了,但她还没有完全逃离负债危险。
程莉担心复贷,开始记账并合理分配自己的生活费,但这仅持续了几天。自2月27号开学后一个月里,程莉已经用自己的压岁钱支出两千多元,仅在3月21号这一天她就花了244元,这是她开学以来花钱最多的一天。程莉意识到自己的消费习惯仍然存在问题。
与程莉不同,段胜并没有选择向家人寻求帮助。3月9号,他将自己所有的网贷统计出来:总计21100元。段胜从事电商直播的工作,为他带来每月5500元的收入,还完1500元的房租和100元的电话费后,他计划每个月还3000元以上。
“先还利息最高的京东金条,然后是美团,每个月剩余的钱还花呗”,段胜这样规划自己的还款项目。为了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段胜每天记录开销,并且每天只带少量现金,用现金支付,有时一顿饭仅花6元。
目前,段胜结清了朋友贷,还了一点京东金条,将债务降到了17000,他预计自己能在8月将所有债务还完。
前方
大二在读学生艾琳和白舒也是网贷的用户,她们只使用花呗这一种网贷产品,并且无实质性负债。
艾琳第一次开通花呗是因为在医院看病时余额不够,情急之下开通花呗,当时为她提供了方便。后来她在月底生活费不够时偶尔用一下花呗,一旦下月生活费到了,她会马上将欠的钱还上,因为借贷消费模式让她有负罪感。
白舒同样如此,她每个月最多用三四百元的花呗额度,并且大多时候是在支付时被默认使用了花呗付款,只要发现自己用了花呗之后她就会马上把钱还上,对于花呗等网贷代表的这种超前消费模式,白舒并不认同。
尼尔森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指出,有86.6%的年轻人使用信贷产品,很大一部分人将其视为“支付工具”,有超过半数人都因无法及时还清贷款而身背债务。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全国范围内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飙升至854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几乎占了一半。另外,汇丰银行最近调查也显示,中国90后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18.5:1,该群体欠各种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17433美元;换言之,90后人均负债额度高达12万元人民币。
思考起自己的负债原因,段胜认为主要是自己自制力不强,有虚荣心,并且本身理财意识淡薄,对超前消费认识不足,后来再加上碰巧在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这个节点上增加了超前消费,最终在状态调整期爆发,从而在网贷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程莉也在后来反省时也才意识到,超前消费真的不是她们这些学生能承受得起的。
除此之外,段胜认为网贷公司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网贷公司应当提高审核标准,不要随便批给大学生额度了,看着像是给钱花,实际上害人不浅啊。”
白舒开通花呗,是因为在一次开通某音乐平台会员时发现使用花呗可以优惠6块钱,花呗红包另外又省了2毛钱,并且后续也多是因为误用了花呗支付。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白舒的室友陈静身上,陈静当初也是为了省5元钱而开通了花呗,她发现在很多支付情况下尤其是免密支付的时候,平台都会默认钩上“花呗支付”的选项。白舒发现平台的这种诱导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并不是主动去开通和使用花呗,她认为这种诱导行为应该被禁止,网贷行业需要被整治。
3月17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程莉认为彻底禁止向大学生贷款不是最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建立金钱观念的办法,开放小额贷款,让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适当接触贷款,或许能让大学生对超前消费有更明确的认知,“但这个额度该是多少?”
艾琳和白舒支持降低额度的做法。艾琳认为2000元是个合适的限制额度,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就能还上。艾琳和白舒还表示,如果花呗这样的网贷在大学生群体中被彻底禁止了,她们也绝对不会触碰所谓的“地下钱庄”,而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艾琳也担心会存在申请程序复杂繁琐等问题,“像花呗一样方便的话才会用。”艾琳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知》内容体现了监管机构对于风险管控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是出于对恶性事件频发、学生非理性消费观念以及校园网贷平台操作不规范的担忧与整治。
王兰认为,强监管尽管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压降金融风险,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庞大的大学生金融消费需求问题,加之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的替代作用也较为有限,这种单一供给机制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化解校园贷供需矛盾。
段胜目前还在努力攒钱还款,他决定在8月还完所有贷款后就换工作,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程莉开始规范自己的消费习惯,她刚刚考研失败,准备再考一次,再长远些,她想等工作后有些存款,靠自己买个房子,“一个人住小公寓就挺好,贷款买个窝吧。”(除王兰外,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安越洋
(作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学生)